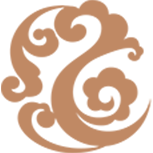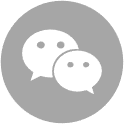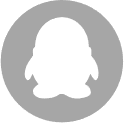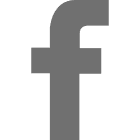汇祥研究
汇祥研究丨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漏罪的量刑处理
2025-03-14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第69条规定的数罪并罚是对判决宣告以前行为人一人犯数罪的一般处罚原则。与之相对,针对判决宣告后发现犯罪分子还有漏罪的情形,《刑法》第70条规定了“先并后减”的处罚原则。依据该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可以看出,对于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情形,《刑法》第70条仅规定了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的处罚原则,但是《刑法》对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发现漏罪的情形没有直接予以规定。针对此类情形的立法空白,为刑法解释和理论研究留下了巨大空间,也在实务中引发了广泛争议。
二、典型案例
作为《刑事审判参考》第1217号指导案例,“朱某某、郭某某诈骗案”的争议就集中于“刑罚执行完毕后对以前未能依法并案处理的犯罪行为如何裁判”的问题。该案中,朱、郭两名被告人曾于2013年因犯诈骗罪均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2015年二人刑满释放。2016年,检察机关以朱、郭二人于2012年共同实施的一起诈骗事实(漏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检察机关于一审宣判后抗诉,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该案在审理中,对于二人所犯漏罪的量刑处理有两种观点:
1.数罪并罚,即参照《刑法》第70条之规定,对于二人所犯漏罪采取与已经执行完毕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
2.单独定罪量刑,即否定参照适用《刑法》第70条或71条的路径,坚持对后发现的漏罪单独定罪量刑。
该案主审法官持第二种观点,对被告人朱韩英、郭东云的漏罪单独定罪量刑,其理由可归纳为以下4点:第一,《刑事诉讼法》第16条明文列举了刑罚消灭事由,而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漏罪的情形下不存在刑罚消灭事由,也不存在因为已受过刑罚就不再定罪量刑的理由。对行为人的漏罪单独定罪量刑,是坚持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和体现。第二,对漏罪与前罪数罪并罚,不符合《刑法》第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的时间条件,即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第三,被告人的不完整供述导致了漏罪,被告人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不得享受数罪并罚的刑期优惠。第四,采用“先并后减”的数罪并罚规则判处的漏罪刑期不一定比单独定罪量刑的漏罪刑期短。
三、学理纷争
这种对漏罪单独定罪量刑的实务做法,在学界也有相应的理论予以支持,并从学理上将单独定罪量刑的处理方式概括为“分别评价说”。主张“分别评价说”的学者提出,对于刑罚执行后发现的漏罪,应单独处理,即对先前判决的犯罪和漏罪分别进行评价,而不是采用数罪并罚的方式。他们认为,通过区分刑罚裁量方式,可以激励行为人在早期阶段主动坦白所有犯罪事实,从而享受合并处罚的优惠。由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因素通常在犯罪结束时已经确定,因此,“分别评价说”主要从预防刑的角度来论证对漏罪单独处理的合理性。然而,这一理论存在若干问题:
第一,漏罪产生的原因复杂,不总是行为人的责任。办案机关疏忽可能导致漏罪在刑罚执行后才被发现,单独处理这种情况不合理。即使行为人坦白,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未立案。漏罪在刑罚执行前被发现,可能不只是因为坦白。改变刑罚裁量方式,将刑罚执行后发现的漏罪归咎于行为人,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第70条规定的漏罪采用数罪并罚的方式,未体现预防刑的差异。
第二,即使行为人未主动坦白,也不应受到不利判决。坦白可从宽,但不坦白不加重刑罚。未坦白仅反映认罪态度不积极,无法律依据加重刑罚。以刑罚执行完毕为标准,对行为人施以不同刑罚裁量方式,缺乏正当性。犯罪后隐瞒事实是常态,对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未主动坦白不应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
第三,"分别评价说"的论证逻辑存在矛盾。以"朱某某、郭某某诈骗案"为例,该理论认为不适用数罪并罚能鼓励坦白,但同时承认数罪并罚可能对行为人不利。如果数罪并罚可能更不利,那么如何鼓励坦白?反之,如果数罪并罚更不利,是否会导致不坦白?显然,"分别评价说"在论证上无法自洽。
第四,根据“分别评价说”,即使犯罪事实和预防必要性相同,因发现漏罪时间不同,刑罚裁量也会不同,这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采用综合原则处理数罪并罚,这与分别评价的刑罚裁量方式在主刑与漏罪主刑之间存在吸收或限制加重时,会导致刑罚效果的差异。例如,某人因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有期徒刑,漏罪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可判处拘役。若数罪并罚,则不需执行拘役;若单独处理漏罪,则需执行拘役。
四、“数罪并罚”的处理模式
应当明确,犯罪发现时间与刑罚裁决无直接逻辑关系。刑罚后发现的漏罪与《刑法》第70条漏罪在违法性、责任和预防需求上无本质区别。笔者认为,为保持法律体系一致性和刑罚统一性,刑罚后发现的漏罪应实行数罪并罚。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把对漏罪采取与已经执行完毕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的处理模式概括为“数罪并罚说”。
(一)“数罪并罚说”具有正当性根据
首先,“数罪并罚说”解释了刑罚的合理性,强调了满足正义需求和实现预防功能的结合。它要求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个人危险性相匹配,并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之间的矛盾。消极责任主义认为量刑应以责任为上限,先确定责任刑再确定预防刑,而漏罪发现时间与预防刑处理无直接关系。
其次,“数罪并罚说”有助于刑法体系的和谐统一,避免因漏罪发现时间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待遇,维护刑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它也有助于解决共同犯罪行为人的刑罚均衡问题。例如,甲和乙共同犯下A罪和B罪,情节相似,责任刑相同。甲因A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乙因A罪和B罪被数罪并罚后执行6年有期徒刑。而甲因漏罪发现时间较晚,总共需执行8年有期徒刑,这种量刑显然不均衡。若采用“数罪并罚说”,则能实现罪刑相适应。
再次,“数罪并罚说”解决了同种漏罪的重复评价问题。尽管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刑罚过重或纵容犯罪,但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采用综合原则,当主刑为有期徒刑时,适用限制加重原则,根据罪行和预防必要性实现平衡,避免了罪刑不均衡。相比之下,"分别评价说"会加剧同种漏罪的重复评价问题。例如,若前后判决的主刑均超过10年,分别评价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两次超过10年的刑期,这超出了数罪并罚的刑罚上限。
(二)“数罪并罚说”拥有并罚的基础
部分学者主张,刑罚一旦完成执行,后续发现的漏罪不应纳入数罪并罚的范畴,这违背了法律的逻辑。他们认为,先前的判决刑罚执行完毕后,若再有漏罪被发现,由于缺少并罚的前提,便无法满足数罪并罚的要求。然而,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具体理由如下:
一方面,认为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的漏罪缺少并罚基础是错误的,因为漏罪与新罪有本质区别。新罪在前判决刑罚执行后犯下,确实缺乏并罚基础。但漏罪的刑罚裁量不同,根据《刑法》第70条,漏罪的并罚是“先并后减”,前判决的刑罚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数罪并罚的适用。因此,即便前判决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对漏罪仍然可以适用数罪并罚。
另一方面,若认为刑罚执行完毕后发现的漏罪缺少并罚的基础,那么《刑法》第70条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刑法》第70条仅限制漏罪的发现时间为“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并未限制漏罪的宣判时间。也就是说,完全可能漏罪是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的,但宣判时前判决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
有人提出应对《刑法》第70条进行限缩阐释,即若漏罪在宣判时前判决的刑罚已执行完毕,则不应适用数罪并罚。然而,我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从字面解释的角度分析,宣判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发现的漏罪,在前判决刑罚执行完毕后宣判,完全符合《刑法》第70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并未超出其字面意义。其次,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考虑,若《刑法》第70条的适用取决于前判决是否执行完毕,将导致办案速度影响刑罚裁决方式,这显然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办案时限,一审流程的三个阶段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一些案件由于前判决刑期短、漏罪侦查慢,不能适用数罪并罚;而其他案件则可能因为前判决刑期长、漏罪侦查快,反而能享受数罪并罚带来的刑期“优惠”。这种依赖偶然因素来决定刑罚裁决方式的做法显然不妥。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刑事审判参考》第1027号“沈某某、王某盗窃案”、第1028号“王某盗窃案”在内的众多案例也一致认为,即便宣判时前判决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对漏罪进行刑罚裁量时也应适用《刑法》第70条。
综上所述,司法实务对发现刑罚执行完毕之后的漏罪,常常采取单独处理的办法。这种做法的核心原因在于,前次判决的刑罚已经得到执行,并且需要考虑到漏罪与判决后犯新罪的处理保持一致。不过,鉴于刑罚同时包含惩罚和预防的作用,裁决刑罚时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罪行确定、漏罪发现时间与预防必要性无关的情况下,保持刑罚裁量的统一性,可以避免引起公众的不信任。虽然之前判决的刑罚已经执行,但对漏罪实施数罪并罚的量刑和执行仍然具有合理性。漏罪与新罪的本质区别意味着,“分别评价说”虽然在形式上处理了漏罪与新罪的协调问题,实际上却忽略了两者差异,没有实现与新罪处理的实质性一致,导致“判决后刑罚执行前的漏罪”和“刑罚执行后的漏罪”适用不同的刑罚裁量方法。“数罪并罚说”则能根本解决其他方案的问题,避免法规范体系上的不一致。然而,“数罪并罚说”的理论模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不仅包括纵向层面的《刑法》中关于数罪并罚制度及相关规定的澄清,也涵盖了横向层面关于缓刑考验期满后发现漏罪的处理。
律师介绍

隗卓然律师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合伙人、刑事法律事务二部主任、公益与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刑事业务研究会副秘书长,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专家,首都文化体育交流公益基金会首席法律顾问,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文化交流论坛首席法律顾问。
十年刑警生涯,曾任职于某直辖市公安局,涉及刑侦、经侦、情报、法制等多部门。指导、参与办理了大量社会影响重大、案情疑难复杂的普刑类案件和经济犯罪类案件,并多次立功受奖。
2017年辞去公职后,专注刑事业务,代理了多起社会影响力重大的职务类犯罪、经济类犯罪和普刑类案件,部分案件的办理结果开创了近年来的先例。
相关推荐